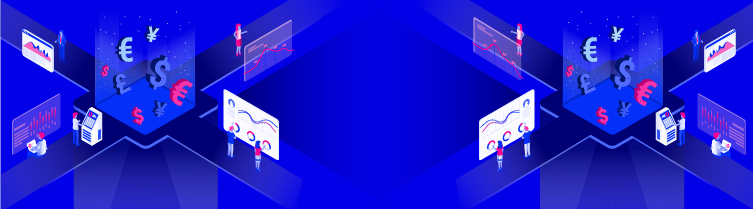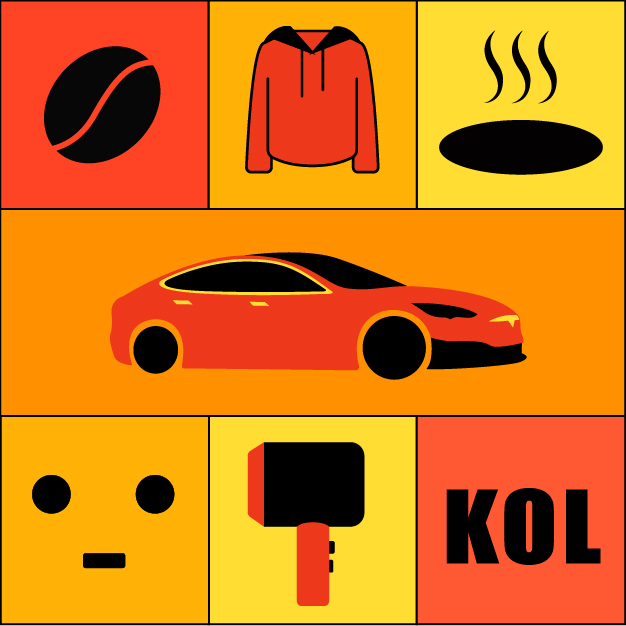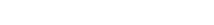惊蛰研究所
惊蛰研究所作者|娅沁
声明|题图来源于网络。惊蛰研究所原创文章,如需转载请留言申请开白。
“我们两年没办年会了,团建也没了。”提到年会的缺席,建筑行业HR刘芳(化名)的情绪并没有任何波澜。过去两年,她所在的公司经历了人力大幅缩减,从过去的两百多人到如今只剩下六十人,并且“春节前还会再减”。刘芳说:“公司能存活下来,按时发工资就很好了。”
近几年,不少企业开启了“年会改革”,曾经雷打不动的年终仪式悄然退场或大幅缩水。当人们谈论它的变化时,语气里没有愤怒,甚至鲜有怀念,只有一种近乎“麻木”的平静。这份平静背后,是一个正在压倒一切的共识——活下去。
一场集体仪式的“退化”
年会曾经是集体归属感的象征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由单位组织的联欢会可以说是年会的雏形:工厂礼堂作为年会场地、员工自发排练节目、单位负责采购瓜子糖果,而举办这场联欢会的核心目的是营造集体归属感。

*电影《年会不能停》剧照
进入二十一世纪,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和经济增长加速,年会迅速演变为企业实力的展示窗口,活动规模和预算不断攀升。然而近年来,受多方因素影响,年会在许多行业中逐渐收缩,甚至消失了。
“从2020年至今,我们公司已经不开庆祝色彩的年会了。”从事电力相关软件工作的江朗(化名)告诉惊蛰研究所,年会虽未完全消失,但公司投入的成本与员工的参与热情均已大幅缩水。
江朗自2013年加入这家公司,至今已十三年。据他回忆,往年公司会租用酒店,先开总结大会,再举行全体晚宴,外地分部的同事也会专程赶来,聚在一起吃饭,还组织节目。但自2020年起,总结会改为线上,大规模聚餐取消,改为各事业部自行安排。“2020到2021年,事业部聚餐规模尚可。2022年后变成小部门聚餐,还明确餐标(人均100元)。基本吃顿饭,也就没什么了。”
与年会“降温”同步发生的,还有公司规模的收缩。江朗透露,公司员工总数已从高峰时的约1500人压缩至目前的900人,且裁员仍在继续。“我们部门都下了优化指标,必须要优化3个人,整个部门现在14个人。”
在传统制造业,年会传统的断档同样明显。任璇(化名)所在的德资汽车零部件供应企业,在连续举办了二十三年年会后,今年决定停办。

任璇在这家德企已工作六年。“公司非常稳定,工龄十五年的老员工很多,连清洁阿姨都待了十六年。”在她看来,年会停办的主要原因在于“没订单了,开不了源,就只能节流。”
任璇告诉惊蛰研究所,以往每年圣诞节前,大概在12月4日左右,公司就会确定年会时间。确定之后,“老外陆续回国度假,有些人到年会时会赶回来。”任璇回忆,过去公司一般会承包假日酒店的一个大厅,不仅邀请外部表演团队,公司内部也组织节目,妆发都有专人打理。每桌餐标约2500至3000元,并穿插抽奖环节。
得知公司今年不举办年会后,任璇只是在社交平台上简短地写了一句:“确定了,公司没年会了。”
下游服务行业,则更直接地感知着这场退潮的寒意。“简单说,一年不如一年。”在酒店行业从业十三年的方昕(化名),目前就职于一家奢华酒店。她告诉惊蛰研究所,每年一月中旬至二月中旬,是年会最集中的时段。过去在一月至春节前的“年会高峰期”,酒店宴会总收入中“基本上70%都来自年会”。

方昕记得,以往最繁忙的周五、周六,所有宴会厅都会被订满。但如今,年会预订量下降了约20%,这一变化从2024年起尤为明显。她表示,如今继续办年会的公司数量在减少,预算在降低,规模也在收缩——部分原因或许是员工总数本身的缩减。
员工和公司,都在变得更现实
年会的淡去与消失背后是企业与员工之间双向的现实选择:公司收紧预算,追求更明确的投入产出;员工也不再看重形式化的仪式,转而关注职业安全与实质回报。
对企业而言,简化或取消年会最直接的动机是控制成本。在经济上行期,企业愿意为一场盛大的年会买单,视其为对员工满意度、团队凝聚力与企业形象的投资。然而当行业进入存量甚至收缩阶段,每一笔支出都需精打细算,追求确定性的回报。年会的“性价比”因此被重新审视。
“主要是减少预算,另一方面也没心情办了,开一次年会也要三四十万。”在建筑行业从事8年人事工作的刘芳告诉惊蛰研究所,她所在的公司自2024年起持续精简人员,从约200人缩减至60人左右,且春节前还会继续减少。
“我们人员主要在项目上。通常一个项目结束后,如果接上新项目,团队就能继续运转。但像这两年接不到新项目,就没办法安排人员工作,实在没办法,只能结束合作。”刘芳坦言,“现在竞争很激烈,为了生存下去,价格压得很低。不说赚多少钱,有活干、保持基本运行就很不错。”
即便仍在举办年会的企业,规模与规格也明显收缩。方昕指出,许多企业在年底依然会举办客户答谢活动,因为“客户才是金主,需要维护”。相比之下,内部员工的年会则“能省就省”。以南京市场为例,往年3000元一桌(10人)的餐标,今年普遍降至2500元。“我们也在调整价格,但不能一味降价形成恶性循环,要在调整价格和提供的附加服务中间做个均衡。”

除了餐饮降级,奖品福利也在缩水。造船业的陈晖(化名)透露,公司年会的奖品价值虽然没变,但中奖比例大幅降低:“原来有一半人能中奖,现在可能总共只有100人能拿到。但是光我们部门就有800多人。”任璇则发现,汽车行业公司年会的头奖价值出现了“腰斩”,过去头奖是市场价值约15000元的笔记本电脑,如今“降格”成了某品牌手机。
在目睹年会不断“缩水”的趋势后,员工对年会的态度也趋于务实,乃至淡漠。一部分人会认为,花钱办年会“不如直接发现金、发福利”;也有人不愿在忙碌一年后,还要为一场内部活动额外付出精力去排练节目、配合气氛。在一部分人眼中,企业年会正从值得期待的年度仪式感变为略显负担的流程性环节。
而对另一部分员工来说,比年会更重要的是公司的生存。“比起吃吃喝喝,更担心明年公司还在不在、会不会裁员。”任璇说,“整个行业现在是夕阳产业,大家都不看好未来。”江朗也表达了类似感受:“我只是把年会当成公司经营和内部氛围的风向标。热闹如果只是粉饰太平,那更加凄凉。我已经接受业绩下滑的事实,未来几年,日子会越来越艰难。”

在与方昕、江朗、刘芳交流的过程中,惊蛰研究所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:如何看待自己公司年会的变化?三人的回答中,分别提到了“平静”“麻木”“理解”。或许这种情绪本身,比消失的年会更值得关注,它意味着,人们已跳过情绪阶段,直接进入了应对现实的处境。
当职场失去“社会时钟”
虽然人们已经开始接受年会的取消或简化,但这并不代表企业员工不再需要它所带来的仪式感与集体温暖。只是当“工作存续”这一基本前提都面临不确定时,对仪式的期待便自动退居其次——生存,先于形式。
“不开年会,产线员工都有点失落,年轻同事还是挺在意年会的。”任璇说,“年会意味着一年工作基本结束,不会再开新订单,员工陆续休假回家过年了。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,大概是忙了一年可以休息的标志吧。”尽管对她自己而言,随着入职年限增长,那份兴奋已渐渐淡去。
刘芳曾负责过多年的年会筹备,包括聚餐、演出、抽奖等环节。“那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非常繁琐操心。从定场地、菜单、奖项、人员到节目安排,整个流程都要反复和领导沟通确认。我一般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准备,年底领导又特别忙。我们通常在小年夜办年会,所有安排都得围着这个时间转。”

尽管不用再操办年会让刘芳觉得轻松,但她坦言仍会怀念年会的气氛——不是筹备的过程,而是大家团聚的时刻。“以前就算有人没抽中奖,公司也会加码,让剩下的人都能拿到红包。开年会是必要的,辛苦了一年,大家一起吃饭、抽奖、看表演,都很开心、放松。”
因此,年会的消失,远不止是一场聚会的缺席。年会更像是一架职场“社会时钟”,在春节这一传统节庆之外,专门为职场人标注出一年工作的正式收官。它的存在,让职场时间变得可感知、可期待。
对于许多企业而言,取消年会并非主动的文化舍弃,而是一种被动的环境适应:预算减轻、规模收缩、仪式感让位于生存现实。这是一种“务实”,却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职场文化的某种“降级”。
若将年会的变迁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,我们所见的不仅是一场聚会的消失,更是宏观经济气候与行业命运的映照。那些依然坚持举办年会、并借此传递增长与信心的企业,在当下显得格外珍贵。是否举办年会,也已成为行业分化的一种标志。

正如方昕所观察到的,仍坚持举办年会的企业多集中在发展相对向好的行业,如科技、半导体、物流等。变化尤其显著的是地产行业,其在市场繁荣期曾是高端酒店的常客,如今已基本停办年会。金融行业以往也偏爱高档场所,现在多数公司不再举办,少数继续举办的企业也更趋低调务实。
在未来,年会的意义或许还将持续演变。它曾作为职场人评估企业实力、景气度乃至是否值得加入的标尺之一,如今却在许多场合褪去光彩。
年会不再只是一种内向的庆祝,而在某种程度上,异化为一个外向的、关于生存能力的标签——有或无,强或弱,映射出一家公司、一个行业甚至一个时代的脉搏。
*文中刘芳、江朗、任璇、方昕、陈晖均为化名